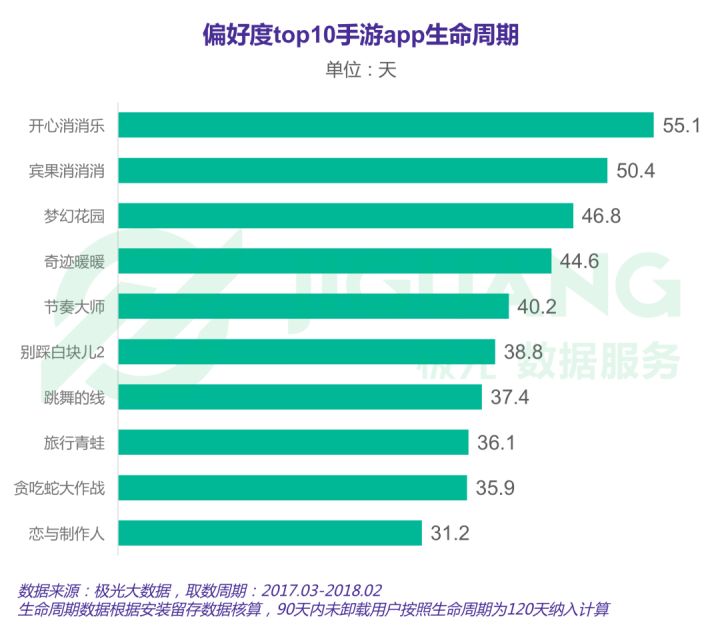到底应该怎样评价冰心?(他人对冰心的评价)
冰心的父亲参加过甲午海战——冰心儿时便被灌输“只有烟台是我们的!”
对日本的仇恨,是家传的!
冰心的父亲与萨镇冰是同僚兼好友。
冰心从小好男装,没扎过耳洞。
冰心读的是教会中学,是正宗的基督徒。
冰心在京于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
冰心1919年开始写问题小说、诗歌、散文。
冰心于二十年代初留美,学英国文学。去时途中写《寄小读者》——我们第一次通过白话文的形式使孩子们开拓了自己的视野。
冰心非常爱孩子,有童心!
冰心的爱情始于去往美国的船上,定情于慰冰湖畔。谨慎地向父亲咨询意见,父母同意。
冰心与吴文藻的证婚人是司徒雷登,因为他是基督教会的著名人士。
冰心夫妻伉俪情深,长寿不是罪过。
冰心确实瞧不起在道德上有些瑕疵的人和事,这不是罪过。有宗教信仰的人多少都存在精神“洁癖”。
冰心于1932年出版《冰心全集》,她是我国第一位出全集的现代女作家。
冰心写了《分》,探讨阶级对立。
冰心是基督徒,但她也是个儿童文学作家。她也写了其他形式的作品。她的作品不追求华美,如她从小不喜欢女装与打扮。
冰心的文风不算柔美,但依然按基督教义宣扬大爱与道义。
她翻译的作品文风现在看来不是最好的。但在当时连白话文的基本语法都不确立的前提下,尝试用白话文翻译国外作品便是一种进步。
冰心在重庆当的官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妇女组织的名誉官职。
冰心和宋美龄是校友,美龄以冰心盛名为由多次邀请冰心当官(冰心本来不想当官,以认床为由推脱,美龄说可空运至重庆——引发林粉讽刺)
冰心在云南的默庐往来无白丁,与西南联大关系密切。
冰心在抗日救国期间写下让人们依然充满希望的诗。
冰心抗日救国有国难家仇的背景。
抗日战争后冰心去日本是陪丈夫随中国驻日代表团去日本调研,吴调研日本战后社会形态,并于此时接触共产党。
冰心在日本教中国文学史。
冰心原来不信共产党,因为她有基督信仰,但她爱国。
冰心当时随夫去日本是在国民党的政权下以官方派遣形式出国。国民党逃至台湾,他们在日本的位置既尴尬又危险。
吴文藻于1950年授聘于美国耶鲁大学,但他没去美国而是借机回国。
冰心在文革被周总理保护。
没人会对救自己于危难之中的人大加讽刺……不亲共不符合当时社会思潮。作家也需要支持才能发声——这比较复杂。
冰心活到八十岁骨折,写下《生命从八十岁开始》
冰心的儿子确实出轨,但这是私德,不能把所以责难抛给当时六七十岁的冰心老人。
冰心的孙子确实行为不妥,但他不信基督教,没人能约束他的个人行为。
总结:她确实长相不美,但她内心纯净;她确实有宗教信仰,但她亲共产党;她确实写的不美,但她胜在时代的前面;她确实长寿,但她从年轻时也饱受病痛折磨;她的专业是英国文学,但她努力在国外宣传中国文学;她没进西南联大,但西南联大的人出现在她的家里;她当官,却是宣传抗日救国的官;她写小桔灯,谁说没在当时的国难当头感受到一丝希望?
她写儿童文学,那是某些从孩子的世界中“摆脱”出来的人们不愿意重视的净土!
她追随红色,不代表她没有良知;她讽刺林,代表她有“慎独”的底线!
你们看不上的儿童文学,是早期儿童最需要的精神家园!因为她需要给孩子们带来希望,因为孩子是国家的未来!
你们说19岁的诗不像诗,你们说冰心靠报社的编辑亲戚发文章?报社人多了去了,出了几个冰心?当时立场从文的女青年会写,怎么不如冰心多写多发?在数量和质量上超过冰心?
欲加之罪,就是脱离时代特有的背景,张狂地胡说八道!
不懂宗教教义,就对有宗教信仰的作品横加贬低!真是新时代的文化人!
噢对呀,现在的孩子越来越不喜欢冰心的《寄小读者》了——因为现在孩子们太容易打开自己的视野,时代不一样,环境不一样,有电视有网络,甚至可以自己出国游历世界,谁还在乎冰心笔下的描绘?
你们吃了几天饱饭,大概忘记了她参加的五四运动,忘记了她父亲在甲午海战时的流血牺牲!你们宣传的张爱玲,爱上的是一个在日伪期间替汪伪政府执笔的文人!
才有机会读了几天党喉舌之外的闲文,才那么牛逼地排斥亲红的文章,吹捧张的《秧歌》?
才读了多少书就觉得前人的书不入你们的眼了,你们在当时的境地下,以当时的知识储备能写出来一句顺溜话不?用磨炼了近百年的白话文文法去评判当时不成熟的语言文句还真是堂而皇之!
真是无知者无畏!
社会道德,不管是公德或是私德,大概在一种所谓真爱粉的眼里都不算什么!
你们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