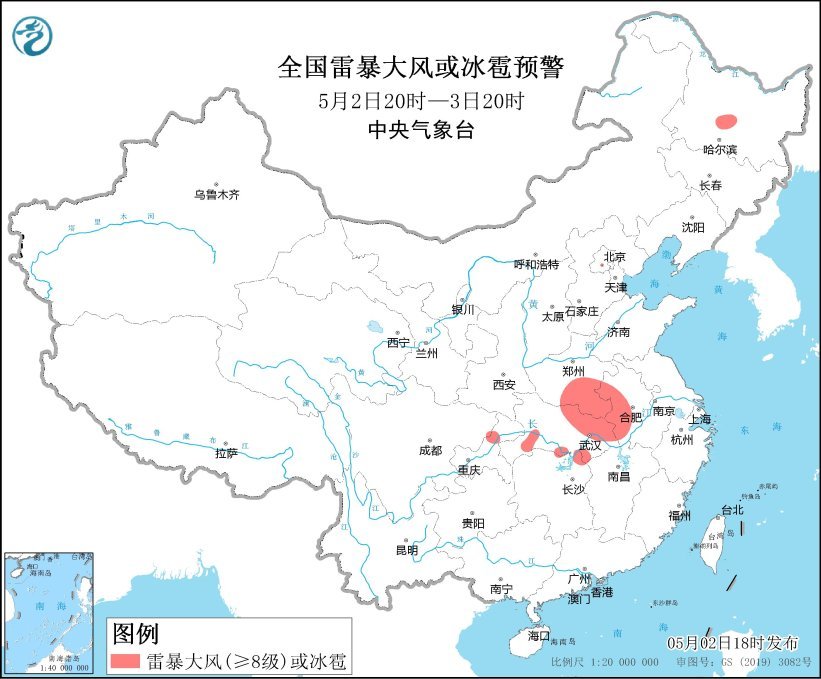分析十七年文学中宗璞的短篇小说《红豆》-宗璞的短篇小说《红豆》原文在线阅读下载
这个是,好不容易写(划掉)摘抄出来的当代文学史作业 一条分界线
———————————————————————————
个人感情在时代巨变中做出的选择
——分析十七年文学中宗璞的短篇小说《红豆》
十七年文学是指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文革”开始,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历程,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时期。十七年文学作品呈现了“又红又专”的鲜明特点,政治性凌驾在文学性之上,它们承担了在建国之初的特殊历史内容,这一点无可厚非。不可否认,这个时期也产生了许多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如《保卫延安》、《红旗谱》、《红日》、《创业史》、《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等等。而《红豆》这部短篇小说,运用的是在校园爱情中展现时代巨变方式,它里面的故事情节深深地吸引了我。
《红豆》这篇小说的作者宗璞,原名冯钟璞,为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这可能对她自己“诚”与“雅”的文学创作特点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她从大学开始创作小说,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她以自己熟悉的知识分子和校园生活为题材,创作小说来表现知识分子在时代巨变的十字路口的内心搏斗。在当年的年底,她完成了小说《红豆》,并载于《人民文学》1957年第7期上。
这篇小说采用倒叙的笔法,从女主人公江玫时六年重回大学校园任职党委会干部,翻出藏在耶稣像后小洞的两枚发夹上残余的红豆而回忆起往事为引子,讲述了1948年,在北京解放前夕,大学生江玫与恋人齐虹由于生活态度和政治立场的分歧而导致最终分手的恋情,还有江玫与同屋好友萧素的友情,从而展现了在时代巨变面前,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艰辛而曲折的心灵历程。全篇充满温馨浪漫的情调和浓郁含蓄的人情味,不仅体现了时代特征,整体上还呈现出一种唯美细腻的风格。
《红豆》中的男主人公齐虹满足了让所有春心荡漾女子心动的条件。他温文尔雅,“有着一张清秀的象牙色的脸”,“学物理,弹得一手好钢琴”。齐虹与江玫初遇是在走向练琴室的路上,邂逅相遇,展开恋爱。他不但通晓音乐,还熟谙苏轼、莎士比亚的爱情诗句,“你甜蜜的爱,就是珍宝,我不屑把处境与帝王对调”,这样一个自由主义者,让江玫爱得如痴如醉。
而江玫的室友萧素则是作为江玫的革命启蒙导师,对江玫走上革命道路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她鼓励江玫去朗诵艾青的诗歌《火把》,让她参加墙报抄写、游行救护等工作。江玫从萧素的身上看到革命的力量,意识到萧素的生活是和千百万人联系在一起的,从而产生了对共产党的认同。她不但开启了江玫对革命的认识,也对江玫的爱情提出忠告:“他有的是疯狂占有的爱,事实上他爱的还是自己。”
小说对情节的构造也十分巧妙,齐虹和萧素的出场就像“你方唱罢我登场”,两者的情节冲突是交替出现的,这也表现了江玫内心的摇摆不定。而在我看来,萧素对江玫产生的影响比齐虹的大。江玫本身就比较关心政治局势,萧素具有泼辣坦率、正直无私的性格,她身体力行投入革命潮流的举动深深影响了江玫。在江玫的母亲生病时,她领头卖血为江母筹款。而齐虹的极度以自我为中心和强烈的占有欲和控制欲让江玫一度怀疑他们的感情,“好像江玫是他的一本书,或者一件仪器”,“他监视着爱情,监视着幸福,监视着江玫”。
而小说高潮所写的两件事让江玫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而放弃与齐虹的爱情。首先是北京解放前夕,萧素突然被捕,齐虹的反应却是“干那些民主活动,有什么好下场!”这让江玫清楚地意识到两人间的鸿沟无法跨越。而让江玫坚定与齐虹分手的转折点便是江玫得知父亲死亡的真相——十五年前因思想罪被抓走,“不明不白地就再没有回来”。父亲的屈死和母亲的眼泪,切身的家庭悲剧,让江玫更清楚自己的人生选择,“这种爱情,就像碎玻璃一样割着人”。最后,在国仇家恨的交错下,她坚定地拒绝与齐虹一起去美国,以“我不后悔”为两人的爱情画下了句点。
作者在小说中运用了大量象征、隐喻等手法,尤其明显的便是发夹上的两枚红豆。这件物品在小说不同位置的出现,有着独特的象征含义。开头江玫从藏在耶稣受难像后拿出残损的两粒红豆,象征着江玫打开尘封的回忆。第二次出现是在初遇齐虹之前插入描述托着两粒红豆旧式发夹的来历——是母亲从箱底找出,“她的新同屋萧素说好看,硬给她戴在头上的”,同时介绍了萧素在江玫人生中的重要性。第三次是在江玫因要帮萧素看漫画拒绝与齐虹出去玩,与齐虹推搡中红豆发夹落在地上,被齐虹踩碎。而齐虹将两枚红豆装在盒子里放在耶稣像后的小洞与开头相呼应。此时发夹碎了象征着江玫齐虹感情出现破裂,而收好红豆又是隐喻着江玫当时认为两人感情有挽回的余地。第四次是两人在房间作最后告别出现一句“江玫看着那耶稣受难的像,她仿佛看见那像后的两枚红豆”,表现了江玫对这份爱情的不舍与无奈。结尾最后写到“她把红豆和盒子放在一旁”,表现了江玫的放下大学时代与齐虹的感情,成长为一名成熟的革命工作者。
此外,“粉红色的夹竹桃”作为江玫安稳生活的比喻,见证了她走出象牙塔逐渐成长的过程。从不谙世事,“母亲从摆着夹竹桃的台阶上走下来迎接她,生活就像那粉红色的夹竹桃一样与世隔绝”,到在遭受爱情磨难,眼见母亲病重,得知好友被捕,发现父亲之死的真相后,她平静的生活彻底粉碎,这时“借着闪电的惨白的光辉煌,看见窗外阶上夹竹桃被风刮到阶下”,值得一提的是“小鸟儿”是萧素给江玫取的昵称,小鸟飞出粉红色夹竹桃的过程,便是她从不谙世事的大学生到成熟的革命工作者的成长的过程。
小说所具有的诗化意境,使整部作品带有细腻而悲思的情愫,散发出诗意的气韵。作品用诗画般的语言尽情地描写江玫与齐虹之间的爱情。例如,“他们散步,散步,看到迎春花染黄了柔软的嫩枝,看到亭亭的荷叶铺满了池塘,他们曾迷失在荷花清远的微香中,也曾迷在桂花浓酽的甜香中,然后又是雪花飞舞的冬天”,以大自然的生机活力来表现青年人爱情的甜蜜;约会被齐虹说成“接你到‘绝域’去做春季大扫除”,“‘绝域’是他们两个都喜欢的一个童话,潘彼得中的神仙领域。他们的爱情就建筑在这些并不存在的童话,终究要萎谢的花朵,要散的云,会缺的月上”,体现了他们爱情的浪漫与缥缈。而江玫因红豆而引发的怀旧情绪和情不自禁的泪水,则使作品带有一种温情脉脉的感伤美。
小说将男女恋爱中的暧昧和情动表现到了极致,就像是古早言情小说桥段的奠基作品。小说中运用语言描写和心理活动将齐虹和江玫的爱意刻画得浓烈而真挚,在江玫反问齐虹“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齐虹轻轻地说:“我生来就知道”,暧昧于语中产生。“江玫还没有想到要忘记齐虹,他不知怎么就闯入了她的生命,她也永不会知道该如何把他赶出去”,则用江玫的心理写出了她对结束爱情的犹豫。
齐虹和萧素,分别带给了江玫于小资恋爱与革命生活两条不同的道路,而时代逼迫她一定要在这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这两种力量对江玫进行着完全相反的牵引,萧素将她带入一个全新的天地,促成一个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少女走入广阔的社会,齐虹则是以爱和艺术的力量力图将她带入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狭小的世界。作者非常细腻地描写了江玫在这两个方面的感情变化过程。
对于江玫造成人生重大影响的两股力量,作家并没有拘囿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基于一种苍白的观念进行概念化处理,做出简单价值判断。萧素让江玫感到她是给人以安慰、知识和力量,通过一种人性的关怀把她带入一个新天地。而对于齐虹,作者对他自私、专横本性的暴露也处理为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贴上一个基于阶级分析的标签。作者同样注意到在恋爱过程中江玫、齐虹两方性格多重侧面的表现,彰显出人性的复杂。即使江玫最终选择的是投入革命与社会建设当中,但是在此过程中,作者仍表现了江玫对这份甜蜜爱恋的依依不舍。
程蔷在《她心头火光熠熠,笔下清风习习——评宗璞的小说创作》中说:“它是把恋爱放在新、旧时代殊死搏斗、即将交替的背景上来写的,它把男女主人公决裂的原因主要归之于他们的政治立场的无法调和。”她主要是从爱情与革命的角度,分析了《红豆》主题中的政治倾向性。但我认为,《红豆》就是一篇爱情小说,政治背景影响了女主人公江玫的个人选择,使她放弃罗曼蒂克般的爱情,为祖国的建设和发展出一份力。我更倾向于《红豆》的主题是未完成的爱,陈素琰在《论宗璞》中说:“《红豆》写的是一个真挚的,富有悲欢苦乐的复杂的内心故事。”陈素琰认为的《红豆》侧重于书写真挚感情,书写充满悲欢离合的爱情,《红豆》不同于概念化,公式化地描写革命给人带来的改变,而是从主人公的感情选择中窥得一二,我觉得这便是《红豆》在十七年文学吸睛的一大要素。
宗璞创作《红豆》,其中虽然对个人感情进行了真挚细腻的刻画,但是她也没有抛弃其中国家民族的语义,女主人公江玫的爱情悲剧结尾,正是她走上正确道路的美好结局的体现,这便是与十七年文学主流一致的书写。《红豆》做到了对个人在时代巨变中做出正确选择的描写,也做到了对革命和爱情进行另类书写。
参考文献:
孙仲英:主流话语下潜在的女性话语.四川外语学院,硕士论文,2010年
宋如珊.论宗璞小说《红豆》的人物塑造[J] 《江汉论坛》 , 2010 (4) :126-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