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质的老座钟摆在堂屋的八仙桌上,钟摆左右摇晃,每一次摆动都带着沉稳的声响,像是在为时光刻下印记。钟面上的罗马数字早已被岁月磨得有些模糊,可时针与分针依旧循着固定的轨迹转动,一圈又一圈,从不曾停歇。这便是记忆里最早感知到的周期,无需刻意提醒,却渗透在日子的每一个缝隙里,让寻常的时光有了可循的节奏。
奶奶总说,过日子就像钟摆,有来有回才踏实。她的针线笸箩里,永远放着半块打了补丁的粗布,每当农闲的午后,她便坐在竹椅上,穿针引线,将碎布拼成一个个菱形的图案。那些碎布颜色各异,有早年蓝布衫的边角,有孩子们旧棉袄的碎花,可在她手中,经过一针一线的缝合,总能变成平整的坐垫或是厚实的门帘。而这样的劳作,几乎每个农闲时节都会重复,仿佛与季节达成了某种默契,在固定的时段里,上演着相似却又不同的温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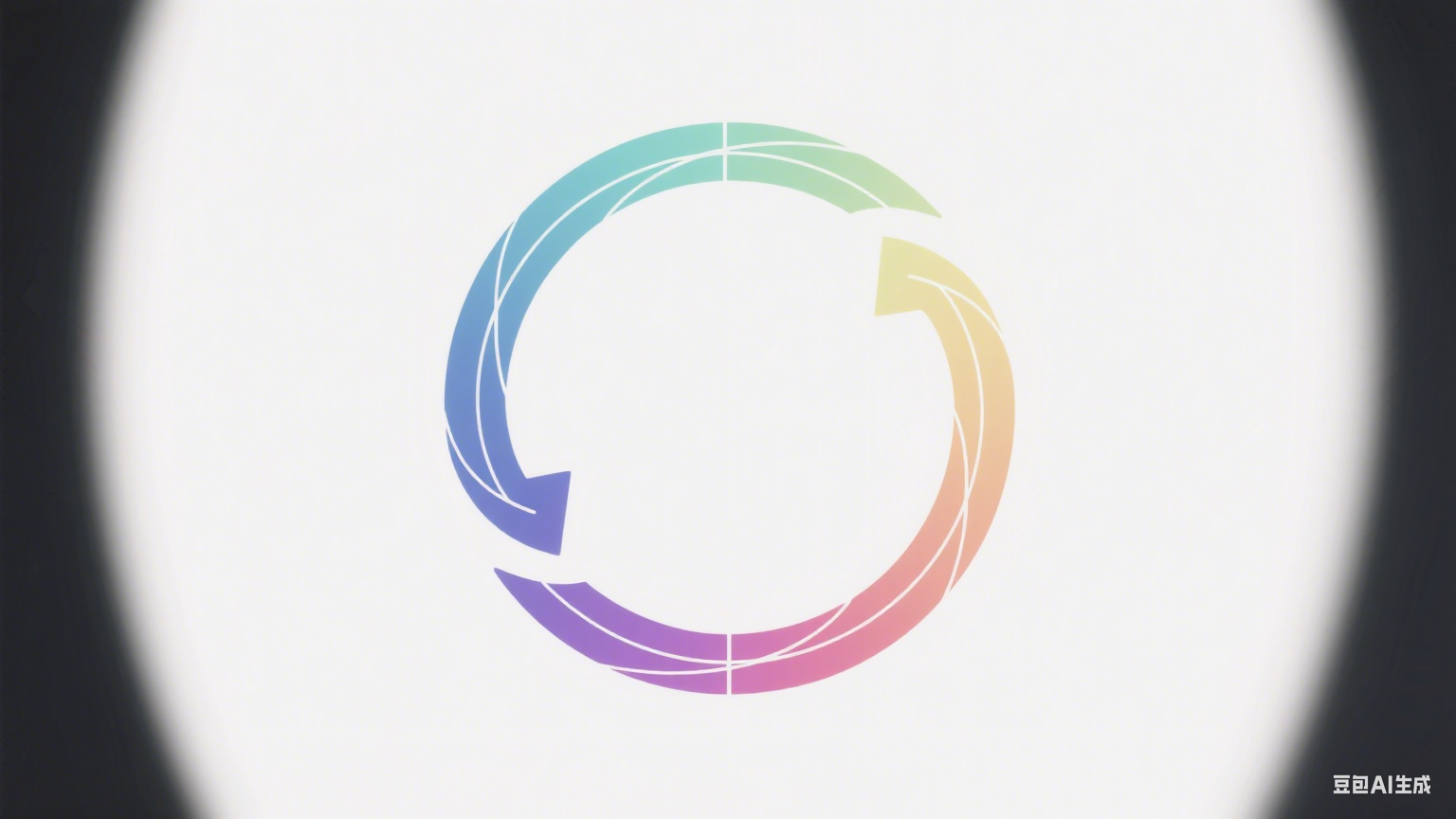
院中的老槐树,更是周期最好的见证者。每年开春,枝桠上先是冒出点点嫩绿的芽苞,像是沉睡了一冬的生命终于苏醒;没过多久,嫩绿便成了深绿,枝叶繁茂得能遮住半个院子,夏日的蝉鸣便在这浓荫里此起彼伏;等到秋风起,深绿又渐渐染上金黄,一片片叶子随风飘落,铺在院子的青砖地上,像是给地面盖了层柔软的毯子;冬日来临,树枝变得光秃秃的,只余下遒劲的枝干指向天空,等待着下一个春天的到来。一年又一年,老槐树就这样循着四季的周期,重复着抽芽、开花、落叶、休眠的过程,而我们的童年,也在这树影的更迭里,悄悄长大了。
小时候住的巷子,每到月末的最后一个赶集日,总会变得格外热闹。天还没亮透,巷口就传来了商贩的吆喝声,有卖糖葫芦的,冰糖裹着山楂,红得透亮;有卖棉花糖的,一勺白糖放进机器里,转眼就变成了蓬松的白色云朵;还有卖老布鞋的,鞋面上绣着简单的花纹,鞋底是一针一线纳出来的,厚实又舒服。大人们会带着竹篮,去集市上买些当月需要的生活用品,孩子们则跟在后面,眼睛盯着那些好吃好玩的东西,吵着闹着要大人买。等到太阳升到头顶,集市上的人渐渐少了,商贩们收拾好摊位,巷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只留下空气中还未散去的糖葫芦甜香,等待着下一个月末的集市。这样的周期,陪伴了我整个童年,直到后来搬离巷子,还常常在梦里想起那热闹的赶集日。
家里的老灶台,也是按周期运转的。每天清晨,奶奶会先把灶台里的灰烬清理干净,然后添上柴火,点燃火种,火苗舔舐着锅底,很快,锅里就冒出了热气,蒸馒头的香味或是熬粥的清香,便会弥漫整个屋子。中午和晚上,灶台又会再次忙碌起来,炒菜的滋滋声、炖肉的咕嘟声,交织成最温馨的生活乐章。到了过年的时候,灶台更是忙得不可开交,蒸年糕、炸丸子、炖排骨,一天到晚都不停歇,直到年三十的晚上,一家人围着桌子吃上年夜饭,灶台才算是暂时歇了下来。可没过几天,等到正月里走亲访友,灶台又会重新忙碌,为招待客人准备可口的饭菜。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周期,让老灶台成了家里最有烟火气的地方,也让每一顿饭都充满了家的味道。
旧时候的日历,也是周期的另一种呈现。那种用宣纸印刷的老式日历,一页纸上印着日期、节气,还有简单的吉祥图案。每天早上,爷爷都会撕下一页日历,然后对着上面的节气念叨几句,比如 “今日立春,该准备春耕了”,或是 “到了冬至,该吃饺子了”。撕下来的日历也不会浪费,有的用来擦桌子,有的用来包东西,还有的被孩子们收集起来,叠成纸飞机或是纸船。等到一年的最后一天,日历就剩下薄薄的一页,爷爷会把它撕下来,然后换上一本新的日历,新的一页上,又印着全新的日期和节气,等待着新一年的时光流转。一本日历,从厚到薄,再到被新的日历取代,这便是一年的周期,简单却又充满仪式感。
如今,老座钟早已停摆,钟摆不再摇晃,可它依旧摆在老家的八仙桌上,像是在默默守护着那些关于周期的记忆;老槐树还在院子里,每年春天依旧会抽出新芽,只是树下玩耍的孩子,早已长大成人,离开了家乡;巷子口的集市,也因为城市的发展,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宽敞的马路和高楼大厦;老灶台虽然还在,却很少再燃起柴火,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家人才会偶尔用它煮上一锅饺子,重温儿时的味道;老式的宣纸日历,也被电子日历取代,轻轻一点,就能看到日期和节气,却少了那份撕日历的仪式感。
可即便如此,那些藏在旧物里的周期韵律,却从未真正消失。它变成了春天里第一朵花开的惊喜,变成了秋天里第一片落叶的感伤;变成了过年时家家户户贴春联的热闹,变成了中秋时一家人赏月吃月饼的团圆;变成了我们长大后,每到某个熟悉的日子,心中涌起的对旧时光的怀念。时光在流转,旧物在变迁,可周期依旧,就像钟摆的轨迹,一圈又一圈,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让我们在时光的轮回里,总能找到熟悉的温暖,也总能期待着下一个美好的开始。不知道当我们再次回望这些旧时光里的周期时,又会在其中找到怎样属于自己的独特记忆呢?
免责声明:文章内容来自互联网,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真实性请自行鉴别,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有侵权等情况,请与本站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