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衣柜最底层压着件灰蓝色毛衣,袖口磨出细密的毛边,领口卷成松弛的波浪。每次换季翻找衣物时,指尖总会先触到它粗糙的肌理,像摸到岁月褪下的痂。
十六岁那个冬天来得格外早,第一场雪落时我还穿着单薄的校服外套。晚自习后缩着脖子往家走,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哈出的白气刚飘到眼前就散了。楼道里的声控灯忽明忽暗,推开门的瞬间,暖黄的光裹着羊毛的气息涌过来。母亲正坐在沙发上绕线团,竹制的棒针在她膝间翻飞,银亮的线轴在地毯上转着圈,滚到我脚边时轻轻一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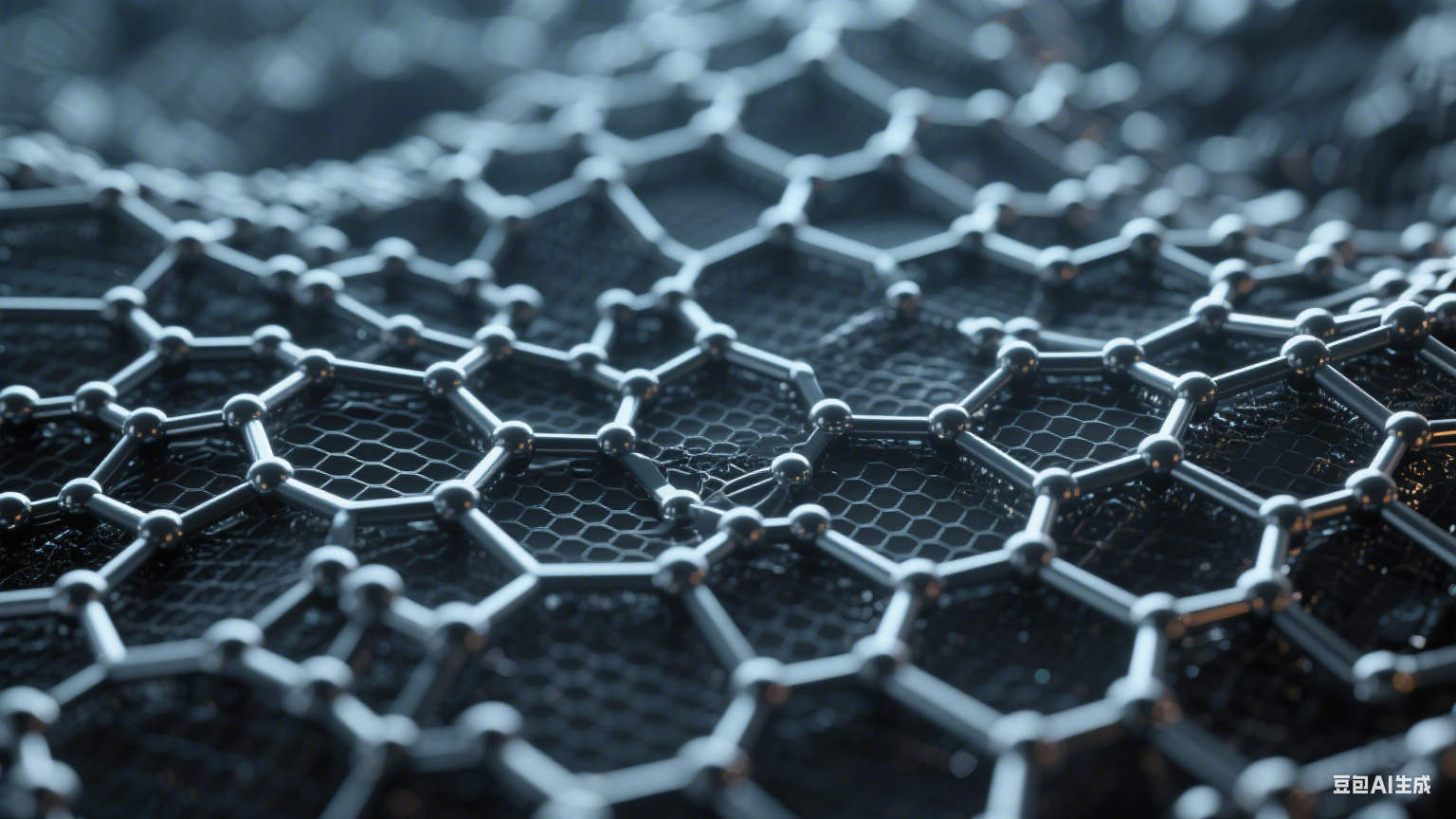
“试试?” 她举起刚织到腋下的半成品,针脚歪歪扭扭的,像刚学步的孩子踩出的脚印。我拽着袖口往身上套,粗硬的羊毛扎得脖子发痒,却忍不住把下巴埋进领口。毛线里混着淡淡的樟脑香,那是母亲把旧毛线拆洗后重新染色的味道,水蓝色褪成灰调,倒比新线多了层温柔的朦胧。
后来每个夜晚,客厅的灯总要亮到后半夜。我趴在书桌前写作业,总能听见棒针碰撞的哒哒声,像春蚕在啃食桑叶。有次起夜撞见母亲歪在沙发上打盹,手里还攥着没织完的袖子,月光从窗帘缝钻进来,在她鬓角的白发上投下细碎的光斑。我轻手轻脚地拿毯子盖她身上,发现她指关节处缠着创可贴,毛线针戳出的小伤口还在渗血。
那年春节我穿着这件毛衣去走亲戚,表妹指着我胳膊上的纹路笑:“这花纹像被猫抓过似的。” 母亲在一旁削苹果,刀刃顿了顿,果皮连成的线突然断了。我把表妹的手拨开,故意挺了挺胸膛:“这是独一无二的设计。” 其实我知道,那些歪扭的针脚里藏着多少个盹睡,多少回拆线重来。
高三冲刺的日子里,这件毛衣成了我的战袍。凌晨五点的早读课,我把冰凉的手缩进袖管,羊毛纤维里还残留着阳光晒过的暖意。模拟考失利的那天,我窝在房间里掉眼泪,母亲进来时没说话,只是把毛衣重新熨烫了一遍。蒸汽熨斗划过衣摆时,那些顽固的褶皱慢慢舒展开,像她欲言又止的安慰。
大学报到那天,母亲非要把这件毛衣塞进我的行李箱。“北方冬天冷。” 她边说边往里面塞樟脑丸,塑料纸的窸窣声里,我看见她眼角的皱纹比毛衣的纹路还要深。宿舍衣柜里挂满了光鲜的新款,这件灰蓝色的旧物被我压在最底下,直到某个寒潮突袭的夜晚,我翻出来套在身上,忽然闻到熟悉的樟脑香,眼泪毫无预兆地砸在起球的衣襟上。
工作后搬家三次,扔了无数旧物,唯独这件毛衣始终跟着我。去年冬天带它去干洗店,店员捏着领口直皱眉:“这都磨成这样了,还洗得出来吗?” 我摸着袖口那些被岁月磨出的毛球,像摸着母亲日渐佝偻的背脊。阳光穿过干洗店的玻璃窗,在毛衣上投下网状的阴影,那些交错的纹路里,藏着整个青春期的温度。
前几日视频时,母亲正坐在窗边择菜,鬓角的白发比去年又多了些。“那件毛衣该扔了吧?” 她抬头时,阳光恰好落在她浑浊的眼睛里。我把镜头对准衣柜,灰蓝色的衣角从一堆衣物里探出来,像个倔强的旧识。“再穿几年。” 我说着,突然发现自己的指关节,也开始像她当年那样,在换季时隐隐作痛。
窗外的梧桐叶又黄了,风卷着落叶敲打着玻璃。我把这件毛衣搭在椅背上,夕阳的金辉漫过那些歪扭的针脚,在地板上织出一片晃动的光斑。恍惚间又听见棒针碰撞的哒哒声,混着母亲的呼吸声,从遥远的岁月里传来。
免责声明:文章内容来自互联网,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真实性请自行鉴别,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有侵权等情况,请与本站联系删除。
转载请注明出处:那件起球的旧毛衣 https://www.7ca.cn/zsbk/zt/5906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