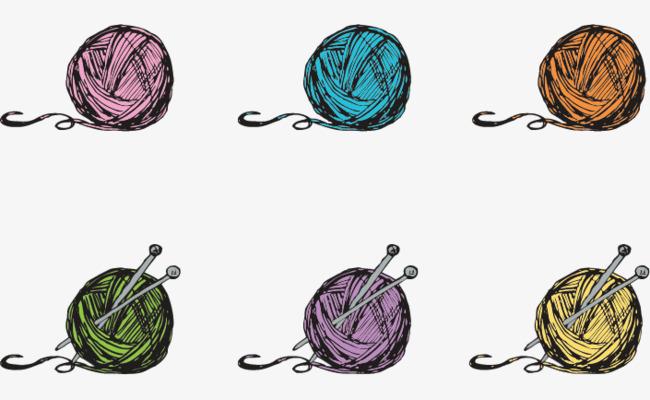
第一次拿起钩针时,我差点把它当成拆快递的小刀。那根银亮亮的金属钩针在手里转了三圈,最后还是直直戳进毛线团里,像只迷路的蚯蚓一头扎进松软的土壤。旁边卖毛线的阿姨笑得直拍大腿,说姑娘你这是给毛线 “打针” 呢,钩针得像挠痒痒似的勾着线走。
现在想想,钩针这小东西真神奇。明明只是根带钩子的金属条,配上五颜六色的毛线,就能变出茶杯垫、围巾、小熊玩偶,甚至有人用它钩出了能穿的婚纱。我见过最绝的作品是个半人高的龙猫,肚子圆滚滚的能当靠垫,胡须是用钓鱼线做的,风一吹还会轻轻晃,当时就看呆了,站在人家摊位前挪不动脚。
刚开始学钩针那阵,我天天抱着毛线团跟它较劲。钩围巾时总把辫子针钩得忽长忽短,织到半米长才发现一边高一边低,活像条被踩过的毛毛虫。有次想给闺蜜钩个草莓挂件,结果钩出个四不像,闺蜜收到后愣了三秒,说这是不是基因突变的小土豆?气得我当场把那团粉色毛线拆了重织,拆到半夜眼睛都快粘在一起,手里的钩针还在机械地运作。
后来慢慢摸到门道,才发现钩针其实很懂 “循序渐进”。先从最基础的短针练起,像搭积木似的一针针往上摞,等手指灵活了再学中长针、长针,就像学写字先练笔画再组字。现在我能一边看剧一边钩杯套,手指像在跳自编的小舞蹈,钩完还会得意地举起来跟屏幕里的主角 “炫耀”。
小区里有位张阿姨是钩针高手,她的阳台总堆着各种颜色的毛线,像个迷你彩虹仓库。每次路过都能看见她坐在小马扎上,钩针在手里转得比魔术师的道具还溜。有次我拿着歪歪扭扭的小熊挂件请教她,她接过来看了看,没说哪里不好,反而指着小熊的歪鼻子说:”这模样多有个性,就像邻居家那个总爱皱鼻子的小丫头。”
张阿姨教我钩针不只能做小玩意,还能 “拯救” 生活。她给磨破边的牛仔裤钩了圈花边,旧裤子顿时变得像新买的;把穿旧的毛衣拆成线,钩成厚实的坐垫,冬天坐上去暖乎乎的;甚至用剩下的线头钩成杯垫、钥匙扣,送给邻居们当小礼物。”你看这毛线,就像过日子,碎布头拼拼补补,也能变出好光景。” 张阿姨一边绕线一边说。
去年冬天特别冷,我跟着张阿姨和小区里的其他阿姨一起,用钩针做了好多毛线帽子和围巾。大家凑在活动室里,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天,手里的钩针从没停过。李阿姨钩得最快,她总说自己年轻时在纺织厂上班,这些活计闭着眼睛都能做;刚退休的王老师学得慢,但钩得最认真,每一针都要数好几遍;我呢,就负责给大家递毛线、倒茶水,偶尔插句嘴逗得大家笑个不停。
那些带着手温的毛线制品,最后都送到了山区孩子手里。后来收到志愿者发来的照片,孩子们戴着五颜六色的帽子,脸蛋冻得红扑扑的,却笑得露出豁牙。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帽子上还歪歪扭扭地别着我钩的小草莓 —— 那是我特意留的记号。看着照片,突然觉得手里的钩针好像有了魔法,能把一点点温暖织成大大的拥抱。
现在我的书桌抽屉里,总躺着几根不同型号的钩针,还有半盒没用完的毛线。有时候加班累了,就会摸出它们钩上几针。看着毛线在钩针牵引下慢慢成形,心里的烦躁也跟着一点点被织进纹路里。有次朋友来做客,翻出我钩了一半的兔子挂件,惊讶地说现在还有人玩这个?我笑着举起钩针晃了晃:”这可不是玩,是我的解压神器,比捏泡泡纸过瘾多了。”
其实钩针这东西,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它不需要复杂的工具,一根针一团线就能开工;也不用特意腾出整块时间,等公交、午休时都能钩几针。但它又很考验耐心,急着求成准会出错,非得静下心来,跟着针脚的节奏一点点来。就像生活里那些值得珍惜的小确幸,从来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得靠自己一针一线慢慢织出来。
前几天整理衣柜,翻出刚开始学钩针时的 “作品”:歪歪扭扭的围巾、漏了洞的杯垫、胳膊长短不一的小熊。虽然现在看实在算不上好看,但摸着那些有些粗糙的针脚,突然想起当时钩错了拆、拆了又钩的倔强。就像翻看小时候画的涂鸦,虽然幼稚,却藏着最认真的自己。
下午阳光正好,我找出一团鹅黄色的毛线,捏起最细的那根钩针。想试试钩只小鸡挂件,送给即将出生的小侄女。钩针穿过线圈时,发出轻微的 “嗒” 声,像在跟阳光打招呼。也许等小侄女长大,我会教她用这根钩针,就像张阿姨教我那样,告诉她有些东西看起来简单,却能织出一整个世界的温柔。
免责声明:文章内容来自互联网,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真实性请自行鉴别,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有侵权等情况,请与本站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