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为什么一心要“灭”匈奴?(汉武帝时反击匈奴节节胜利的主要原因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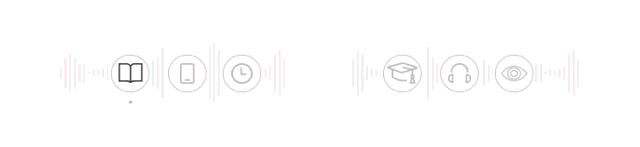
这个问题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诸多历史读者脑中“根深蒂固”,却根本是个“伪命题”,或者说,是一个后人逐步塑造、想象出来的故事。
问题如下:
汉武帝为什么一心要灭匈奴?
他为何独独非要消灭匈奴呢?真的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回答如下:
从真实位面的历史来看,汉武帝从来没有想灭亡匈奴,也没有这个表态,这个问题本身就想象出来的。
汉武帝一朝的“政治理想”或者说“蓝图”,其实在《汉书·武帝纪》中记录的元光元年五月诏书中早已披露无疑:

诏贤良曰:“朕闻昔在唐、虞,画像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乎,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翻译一下大意逻辑,汉武帝向求官的“贤良”问策,特别提出了一个典故,叫“画像而民不犯”,有些“二把刀”翻译成,尧、舜的画像,百姓不敢侵犯,他们以为是纸板警察吗?遍地放圣王的画像……
其实东汉班固在《白虎通》中已有解释:
画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髌者以墨蒙其髌,犯宫者扉,草屦也,大辟者布衣无领。
也就是所谓的“画象为刑”,也就是用衣服模拟“五刑”,不用真砍头、挖膝盖,百姓就不犯法了,这是“圣王时代”的最高境界。
而紧跟着,就提到了西周成王、康王时代的“刑错不用”,也就是“置刑法而不用”,百姓就遵守规矩,甚至于,“圣王”们的德政统治,可以“外放”到四夷臣服、天灾不生,祥瑞排队来现世。
所以,汉武帝感慨了一句:
呜乎,何施而臻此与!
糙点说就是,卧槽,咋干能达到这个成绩啊?
后面,就是基于这个,希望“贤良”能够告诉自己实现的路径,而他的目标也很清晰:
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
简言之,我要比先帝干得更好,上比尧、舜,下比三王,也就是三代的开国君主,夏禹、商汤、周文,今人常把“秦皇汉武”并称,殊不知,汉武帝的眼中,“秦始皇”连根毛都不算,根本不配当标杆,他的目标是上古三代“圣王”。
而这个“伟大目标”的成绩单中,最简单的一项,就是:
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徠服。
也就是说,“四夷来服”只是完成“圣王之治”的一个指标,也是最具现实操作性的指标,而匈奴,又只是“四夷”中的一个,“小把戏”而已。
具体看汉武帝对匈奴战争的表态,意图可以说是一贯的。
见《汉书·武帝纪》记载元朔六年诏书:
朕闻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盖孔子对定公以徠远,哀公以论臣,景公以节用,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朕甚悼之。
翻译过来就是,我听说五帝三代的治道不同,“建德”却是殊途同归的目的,所以孔子对鲁定公、哀公、景公有不同的说法,因为治国的急务不同,所以,我现在一统中国,却坐视北方边境不安定,很痛心啊。
这里,他表态关心的是“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这里的“北边”,特指的是“边境”,而非今天我们常说的“北方”,可以说,他对这场战争的理由,是“安民”,不过,结合之前的“建德”之说,他解释的重点,实际上是强调“建德”的行动顺序,也就是说,在他的逻辑里,这场战争是“内治”的一部分。
之后的变化,《汉书·匈奴传》里记载:
初,汉两将大出围单于,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物故者亦万数,汉马死者十余万匹。匈奴虽病,远去,而汉马亦少,无以复往。单于用赵信计,遣使好辞请和亲。
天子下其议,或言和亲,或言遂臣之。丞相长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为外臣,朝请于边。”汉使敞使于单于。单于闻敞计,大怒,留之不遣。
先是,汉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单于亦辄留汉使相当。汉方复收士马,会票骑将军去病死,于是汉久不北击胡。
这段很长,意思是匈奴被卫霍击败之后,双方两败俱伤,匈奴大败跑了,汉朝也缺马无法再次追击,所以单于派人来请求和亲。(事在元狩六年)
汉朝内部争论,有要和亲的,有让匈奴臣服的,最后皇帝支持了让匈奴臣服的一派,并派“首倡者”任敞为使出使匈奴,去了之后,单于知道是任敞倡议要“臣服”而非“和亲”,急眼了,直接给他扣住了。
这里,汉武帝的态度明显是希望“匈奴为外臣,朝请于边”,也就是向他“臣服”。
再之后,《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于元封元年巡行北疆时给匈奴发的诏书说:
南越王头已县于汉北阙矣。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为!
翻译过来就是,南越王的脑袋已经挂在高阙上了,你匈奴单于有本事打,就赶紧来,汉天子亲自等着你,打不了,赶紧来臣服,藏在漠北苦寒之地干啥呢?
这里,他表态关心的还是“单于臣服”。
《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于元封四年的举动是:
秋,以匈奴弱,可遂臣服,乃遣使说之。单于使来,死京师。
秋天的时候,皇帝认为匈奴衰弱,可以劝他们臣服,所以派了使者,单于的使节来长安,死了……
这里,他表态关心的还是“匈奴臣服”。
对于匈奴单于“臣服”的任何可能,汉武帝都特当回事,《汉书·匈奴传》记载:
杨信既归,汉使王乌等如匈奴。匈奴复谄以甘言,欲多得汉财物,绐王乌曰:“吾欲入汉见天子,面相结为兄弟。”王乌归报汉,汉为单于筑邸于长安。
翻译过来就是,汉使者王乌被匈奴乌维单于忽悠了,说单于想进长安见天子,面相结为兄弟,汉武帝信了,给匈奴单于在长安还建设了府邸(诸侯王在长安有邸)。
这里,汉武帝关心的其实还是单于来朝,哪怕是以“兄弟之盟”也可以,当然,礼仪上要给他降到诸侯王的层次,变相“臣服”也成。(此事应在元封四年前)
唯一一个态度略有不同的是在汉武帝的晚年,《汉书·匈奴传》记载:
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雠,《春秋》大之。”是岁,太初四年也。
这个翻译一下,就是趁着干翻了西域强国大宛,汉武帝想干脆“困胡”,也就是收拾匈奴,所以口号是为汉高祖的平城之围,吕后被冒顿单于写信调戏复仇,并特意拿出了春秋大义,要复九世之仇。
此时,他表态的是“困胡”和“复仇”,就是还要揍你,好好收拾你。
“困胡”和“复仇”,可不是“灭胡”,汉武帝也知道,漠北苦寒,能让不识抬举、不配合自己演“四夷宾服”的“政治秀”的匈奴人难受一下,就不错了,想要一举消灭,高调唱得太高,怕落实不了。
说得更直白一些,汉武帝对于匈奴单于长期以来的“不识抬举”,一定要“报复”一下,但对于“报复”的效果,毫无预期,俗称“出口气”罢了。
综上所述,你会发现,汉武帝从来没有说过,或者表态暗示过,自己要完全消灭匈奴,反倒是非常积极地促使匈奴单于来向他臣服,完成他自己的“四夷宾服”的圣王之梦。
为了这个梦想,汉武帝不惜“百万金市马骨”,见《史记·平准书》:
其秋,浑邪王率数万之众来降,於是汉发车二万乘迎之。既至,受赏,赐及有功之士。是岁费凡百余巨万。
这里的“岁费”当然不只是给这几万匈奴降人的赏赐,还有当年骠骑将军霍去病斩首4万的赏赐,但是给自家将士的赏赐是“一把结”,匈奴降人可不行。
而胡降者皆衣食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藏以赡之。
岁余,会军数出,浑邪王等降,县官费众,仓府空。其明年,贫民大徙,皆仰给县官,无以尽赡。
啥意思?
匈奴降人,所有衣食花费都由国家供应,国家财政不足,汉武帝直接减少自己的“御膳”,把自己驾车的马解下来,出皇帝内府的私产以养活他们。
而由于短期内发动多次战争,匈奴降人又花费巨大,仓储空竭,又过了一年,关东地区发大水,汉武帝开仓放粮根本不够,只能大批迁徙关东贫民七十余万口到关西,尤其是朔方以南“新秦中”,也就是今天的鄂尔多斯,当年的“河南地”。
重点是四个字“无以尽赡”,也就是仓库都空了,总有挨饿的“国民”。
话说白了,就是为了“四夷宾服”的宏大理想,搞得自家的“国民”,“无以尽赡”。而这,发生在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也就是汉军大胜之际。
反观上文中汉武帝对于匈奴单于“臣服”的拉拢表态,却是从元狩六年(前117年,匈奴单于遣使“求和亲”,汉武帝反派出任敞诱其“臣服”)到元封元年(前110年),再一直到太初四年(前101)间没断过,可谓“痴心一片”,哪怕府库空竭、百姓饿死也在所不惜!
至于说“灭”匈奴?殊不知,自古帝王,“外事”不过是“内治”的附属品,成绩单里的一个小条目,甚至只是“营销故事”的一部分,认真,你就输了。

往期精品文章回顾
HOT!:世代友好的两国怎么就闹掰了?
HOT!:帝都富贵地图变迁史
HOT!:大秦帝国的敌人到底是谁?
热点事件
林清玄去世丨收外卖该说谢谢吗丨中产财务自由梦
中华民族象征丨日本战史丨春运如何改变中国
关注知之Known
(ID:Serious-news)
先手获得最新优质文章

以上就是关于《汉武帝为什么一心要“灭”匈奴?(汉武帝时反击匈奴节节胜利的主要原因有)》的全部内容,本文网址:https://www.7ca.cn/baike/36388.shtml,如对您有帮助可以分享给好友,谢谢。
